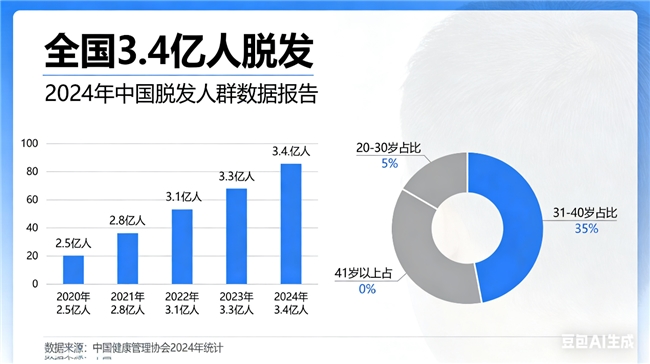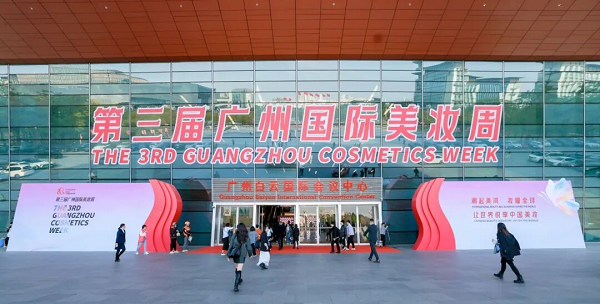结缘河下古镇
河下古镇
常晖
若没有老同学安排的一次运河游,我无缘邂逅河下。
然而我邂逅了它,爱上了它。那年的暖秋,天高云淡,我们在古老而静逸的里运河上泛舟而行。小船飘荡间,芦花摇曳,渔船闲游。离闸口,过榷关,来到一处御码头。登岸,一条绵长不见终点的古巷,即刻闯入视线。巷口一侧有石墙,上刻偌大的四个字“古镇河下”。步入巷内,瞠目结舌:这是何方仙土,何处乐园,竟躲过人间百年变迁,悄无声息、处惊不变地自得其乐?
漫步河下老街,此西邻古运河,东望萧湖,北怀城河的环水小镇,渐如一幅画卷,缓缓启开。原来,这儿曾是漕运重地,元明清几个朝代皆在此设漕运专署。昔日,水上漕艘贾舶,连樯云集,百货山列,巷内人文蔚起,甲第相望,园亭林立。当地人说这方水土“因运河而盛,亦因运河而衰”。在水运发达的年代里,河下作为各类物资集散地,是南北中枢站,其繁华鼎盛之势,无与伦比。
据史料记载,自公元1194年黄河夺淮,淮河流域屢罹水患。明永乐十三年(1415),平江伯陈瑄开清江浦,导淮安城西管家湖(亦称西湖)水入淮,运道改经城西。“河下”遂居管家湖嘴,处黄、运之间,扼漕运要冲,为其咽喉之地。缘其地势卑下,“河下”渐由民间而官方正式得名。
脚踏古老石板,耳听官记野史,眼观百年民居,我在心动。这个陌生的“河下古镇”,朽檐斜梁、柴扉半敛,随处可见酱油作坊,民间纸扎,麻油茶馓铺子,中医世家,糖饼和水糕挑子。没有拥挤人群,没有林立店铺,沿街,住家晒着被子,晾着干菜,摆着瓜果,种着花草,虚着门帘,挂着艾叶,猫狗溜达,棋盘自在。
河下,以其罕见的朴素、真实、闲暇、慵倦和宁静,凝固了光阴,也成就了我无意间挥之不去的情愫。
河下坐落在苏北淮安城。此城如舟,由新、老、夹三城组合,在蜿蜒曲折的文渠间千年生息。若以当地“青莲岗文化”记,淮安已有6,000年历史。此古城乃京杭大运河上的重关,被明人誉为“襟吴带楚客多游,壮丽东南第一州”。而河下,位居其城西北隅,历史亦已长达2,500年。
淮安曾名淮阴、楚州、清江浦、清江、清河、古楚等。那儿曾经出过诸如淮阴侯韩信、《西游记》作者吴承恩和上世纪叱咤风云的外交官周恩来总理等名人。历经世纪沧桑的这方水土,几起几落,自周汉至明清,因京杭大运河、古淮河、里外运河、洪泽湖等各大水道,成为南船北马、北粮南运的集散地。漕运、盐运等河道四通八达,明清皇帝御驾也时常逗留。回望旧时,淮安想必车水马龙,堪称繁华盛世。
然而,这片繁华地到了上世纪,便被人渐渐淡忘。江南人称苏北人为“江北佬”,不乏居高临下的心态。淮安这个水城,比不过池塘纵横、湖泊林立的苏南鱼米之乡,它浩渺的水域无景可言、无戏可唱。“穷乡僻壤”似乎成为苏北的代名词。
我儿时的记忆,是江南的。江南的小河和稻田,江南的湖泊和鱼虾,江南的庭院和软语,江南的青石板和糯米糕,都是定格在脑中的一分温馨和柔软。但周庄和同里等“文化古镇”被发掘后,很多负面印象开始侵蚀回忆。难道人们在有意无意地误读历史?当民居被开放成铺天盖地的店铺和客栈,当游客被淹埋在琳琅满目的商品之间,历史便在车马喧闹里,轰然断层!
无疑,“文化古镇”打着文化的旗帜,竭尽其能,以商业化面貌闪亮登场、招摇过市,是在无情异化历史的真实,刻意修饰人文的语境。曾读到过《文汇读书周报》刊登的一篇张涛甫的文章,文章谈文化的“无用之用”。笔者强调了两种文化的“超重”现象,即要么将文化功利化,要么将文化过度意识形态化。前者的结果是大造所谓文化工程,将文化GDP化,反文化自身的规律性和生命周期,后者则大张旗鼓宣扬文化的纯意识形态性,矫枉过正,违背了文化的民众性、社会性。中国众多的古镇在各地旅游开发的大势中,竞相争艳,却难免千篇一律,可谓怪异的从众心态啊!
而我看见的河下古镇,还在以其原汁原味的市井图撼动人心。它鲜为人知的一隅,默说着昔日,如一朵无需雍容的野花,沁人心脾。这朵花是否会一直开在时代大潮流的边缘,静静地享用被人遗忘之闲?或许,被人遗忘,才能被历史更好地收藏?带着疑虑的心思,我走完了古老的三里路老街。到了街尾,一个答案淑女般款款而来,尚无造作的姿色和逼厌的气势。原来,这个不算镇子的“河下古镇”,业已被悄无声息地打理起来。另一头沿老街饶行的市河和城河等,复建了吴承恩故居和相邻的一些仿古船舫。景致与里运河岸头大不同,却尚能与老街衔接,不障眼,不张扬。
“河下古镇”既成心爱之地,我自然寻思着故地重游。及至再访王兴懋酱园,察吴鞠通中医馆,吃岳家茶馓,尝挑担水糕,又有了口福:在闻名遐迩,建于道光八年(1828年)的“文楼”赏联吃汤包。记得那幅上联是“小大姐,上河下,坐南朝北吃东西”,百年过去,偏偏无人能对。而文楼的“蟹粉汤包”用“九叶诗人”王辛笛的诗句描述,乃“冻肉凝脂拌蟹黄,薄皮敞口一包汤。蒸笼抓取防烫手,齿舌从容着意尝”。
三下河下时,这殷阜之区深厚的医药史,也再次抓住了我的心。江苏中医界有“南孟河、北山阳”之说。山阳,亦淮安古称。山阳的名医竟大多集中在河下,如代表人物温病学家吴鞠通、李厚坤,淮山名医刘金方、张治平、汪筱川,江苏名老中医章湘侯等。医药之外,河下的文人辈出,自唐设立科举制度以来,仅明清两代,河下就出过1名状元,58名进士,100多名举人,且状元(沈坤),榜眼(汪廷珍)、探花(夏曰瑚)三鼎甲齐全。
应该说,河下一带的名人不胜枚举。除韩信、吴承恩和周恩来总理之外,古今还出过汉赋鼻祖枚乘、枚皋父子,文学家陈琳,唐代大诗人赵嘏,北宋苏门四学士之一的张耒,盲人历算家卫朴,画家龚开,南宋巾帼英雄梁红玉与其夫、抗金名将韩世忠,明代抗倭状元沈坤,《老残游记》作者刘鹗,清代礼部尚书、御先生汪廷珍,朴学大师阎若璩,国学大师罗振玉,田园诗人吴进,甲午战争中抗日名将左宝贵,女弹词作家邱心如,水利专家殷自芳,数学家骆腾凤,考据学家吴玉搢,天文地理学家吴玉楫以及船政大臣裴荫森等。
曾与几位当地英杰在“文楼”品茗闲聊,中有一位金老先生。金先生毕生研究楚州史,对河下古镇有其一套理论,即“三三得九”之说:“河下三关”、“河下三儒”以及“河下三不朽”。“河下三关”乃漕关、盐关和榷关,“河下三儒”是儒将、儒医和儒士,“河下三不朽”则为立功、立德、立言。在金先生眼里,河下人个性如水,包容宽厚,刚柔相济,男女皆英。
河下,我心仪的河下,四面环水、魅力独特的河下,愿你既与时俱进,又古风长存!
(责编 凌 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