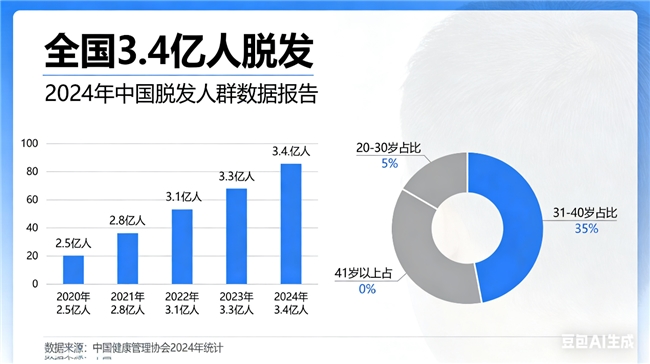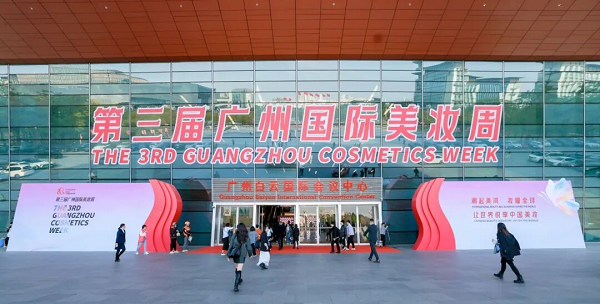文章“署名”中的人格坚守
...基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陈勇钊
给文章“署名”这件事,说起来不是什么大事,但当我们把它和人格、境界这样一些操守联系起来的时候,就能发现在“署名”这样一件小事上,也能展现出大的人生境界来;虽然只是小事一桩,凸显的却是大人格、大境界。
蒋路先生是著名俄苏文学翻译家、人民文学出版社资深编辑。他的身上,具有一种可贵的“甘愿为他人做嫁衣裳”的精神,而且助人不图名、情愿做无名英雄。
由北大李赋宁教授主编,刘意青、罗经国等教授编撰的《欧洲文学史》一书在出版前,曾交由蒋路先生校订,同为编辑的艾珉女士回忆说:“北京大学当时主管《欧洲文学史》工作的罗经国老师告诉我,看了蒋路加工的《欧洲文学史》书稿,他们都感动得说不出话来:整部书稿改得密密麻麻,所有史实或细节,他都已核实订正;结构欠合理处已重新调整,有的段落甚至改写或重写。在他们看来,蒋路远不止是编辑,而且是重要的作者之一,可是请他参与署名时,蒋路却坚决谢绝了。”
学者蓝英年先生也曾在回忆文章中谈到了蒋路的另一件“拒绝署名”的往事:“蒋路对《欧洲文学史》的校订已经充分说明他的欧洲文学史知识何等丰富。此外他从事过《瑞典文学史》和《捷克文学史》的编辑工作,他加工后的《捷克文学史》,质量上有极大的提高,致使编者看后非要他署名不可,他当然又谢绝了。”
翻译家凌芝在《蒋路文存》编后记中也写到:“《生活与美学》的译者周扬主动提出请蒋路将他这本由英文转译的旧译本根据俄文版本再校订。如同改造一幢旧房屋,既要用新材料表现现代感,又要最大限度地保持原有的风貌,这实际意味着比重译一遍还难!可是蒋路做到了。尽管由于年代的久远和当事人的离去,许多细节已无从考究,责编蒋路让这本书获得了新生。成稿时,连俄文版书名《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也恢复了它的原貌。周扬看了改文,十分满意,主动把‘蒋路校三个字写在他名字后面,却被蒋路毫不犹豫地勾掉了。后来周扬再一次把他的名字写进后记,结果照样被勾掉了。”
林增平先生长期致力于辛亥革命历史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成为研究辛亥革命历史的权威。前些年,有关部门决定出版一部《辛亥革命史》,林增平先生受邀承担了其中部分章节的撰写工作,而且,他还与另一位历史学家一起负责了这本书的统稿工作。在这本书第一卷出版前,有的编委提出,要将林增平先生署为第一主编,与会者的一致同意,大家都觉得这是实至名归,没想到,林增平先生却非常反对,坚决不同意将自己作为第一主编。事后,林增平先生曾与孔祥吉先生谈及这件事:“做学问切不可争名逐利。眼睛盯着名利二字,文章就不可能行之久远。”就这样,在林增平先生的一再坚持下,这本书出版时,将另一位学者署名为第一主编。林增平先生的这种淡泊名利、推贤让能的人格风范,感动了许多人。
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先生也曾拒绝过署名。那是1986年,钱学森阅读了一位学者的科研论文,读后给这位学者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这位学者很感激,便主动提出在发表论文时,把钱学森的名字同時署上。钱学森立即回信说:“把我的名字放在文章的作者中是不对的,我决不同意。这不是什么客气,科学论文只能署干实活的人。就算我曾向您提过一两点有用的参考意见,那也只能在文章末尾讲上一句。这是科研论文的原则,好学风,我们务必遵守!至要,至要!”
联想到当下,很多教授,出于不同的目的经常要在学生的科研论文上署上自己的名字,这样的做法,与蒋路、林增平及钱学森相比,境界之高下不言而喻。就如一滴水珠可以折射出太阳的七彩光辉一样,署名这样一件小事,也可以反映出一个人的品质与素养。
如何在现实生活中、在名利面前,保留超越一般人的高尚品质,蒋路、林增平、钱学森三位先生给我们做出了榜样,非常值得我们借鉴和思考。在今天,大众的生活被市场、消费、娱乐、房价乃至网络和新闻所缠绕,正因为这样,坚守对一个人来说显得越来约重要。守住节操,守住作为人的那点单纯与美好。 (责编 李珊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