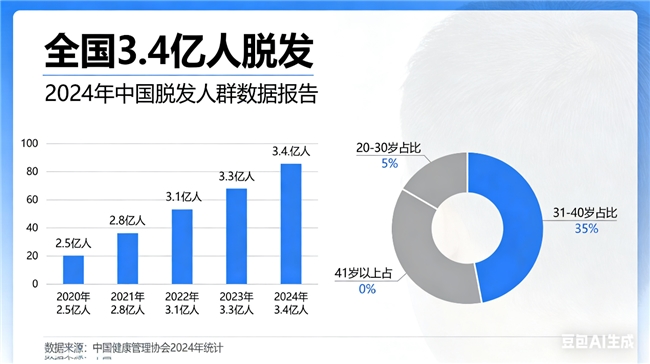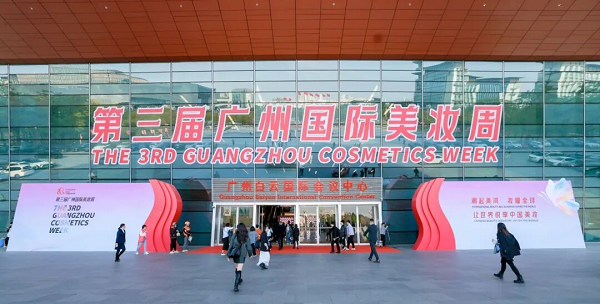习焉不察:教外国人汉语常遇纠葛
老外学汉语热
杨本科
汉语老师的外语
“你是干什么的?”
“教外国人汉语的。”
“哇!那你太厉害了。英语很好吧?会很多种语言吧?”
我作为一名汉语教师,常常遇到这样的问题。这其实是对我们这个职业的一点误解。试想一下,你给小孩子报英语培训班,发现外教每节课都在用流利的汉语讲课,作何感想?
语言是一种工具,所以熟能生巧。从学习方法上来说:重复成天赋。我认识一名水手,他只会说少量的日常英语会话,基本上属于吃喝拉撒买东西之类,但是只要谈起他的专业,轮船的每一部分、甚至零件,他几乎都能用英语说出来。他说,这是他常年在外出海的学习所得。
前年我参加赴东南亚汉语教师志愿者培训的时候,暨南大学的周健教授讲了一个故事:有一个中餐厨师在美国的中餐馆工作了十几年,但是他连基本的英语会话都不会。在语言的学习中,大环境几乎是没有用的,只有小环境才能提高学习者的语言水平。
因此,我有责任、有义务为学生创造良好的语言环境,能用汉语直接表达的,绝不借助其他手段。在课堂上,如果我先说了英文意思,那么中文对于他们来说,将成为一幅幅的图画。所以我必须先说汉语“这是狗”,说过几遍之后,学生依然不明白,他们就会等着我的进一步解释。只有当他们听不懂并且急切地盼望解释的时候,我才能说一点外语,这叫不愤不启、不悱不发。
当然,流利的汉语能将更多的汉语知识和中国文化知识传递给汉语学习者。
“我喜欢学汉语”
前年我在泰国教汉语时,有个学生叫“贡”,是个土生土长的泰国人。她有个远房亲戚是中国人,所以她对汉语很有兴趣。我当时服务的学校叫“中华学校”,名字很中国风,但是能用汉语沟通的人几乎没有。
那一年的下半年,当地教育部门组织了一次演讲比赛。为了增加观赏性,主办方事先给出了几个主题,供参赛选手选择。贡选择了“我喜欢学汉语”。我认为她自己选的题目,应该有很多话要说才对,但是贡说汉语老师是我,指导老师也毫无疑问就是我了。一番推辞之后,最终还是由我来写这篇演讲稿。
我用了一个笑话:有一只老母鸡带着小鸡出来找吃的,碰到一只大花猫。大花猫摁住了一只小鸡,小鸡吓得不停地发抖。这时候老母鸡学了两声狗叫,把大花猫吓跑了!老母鸡得意地回过头来对小鸡说,“孩子们,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学好一门外语是多么的重要啊!”
故事讲完便是一番议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多样的文化。中国和泰国是世代友好的国家,我希望把汉语学好,将来有一天,能到中国走一走看一看,为中泰友谊做出贡献。所以我喜欢学汉语。
大概这样的演讲“三观”很正,于是评委决定把它传到曼谷,最后获得了全泰国学生中文演讲比赛的银奖。
语言素材
翻开汉语教材的第一课,多数课文都是“你好吗”、“我很好”,只是这样的对话在中国人日常生活中几乎不会发生。如果一定要给这句话造个语境,那就得发挥想象力了:当年相爱的恋人分手,后来各自结婚生子,数年后偶然在一个路口相遇,泪眼相望,问一声“你好吗?”回一句“我很好”,然后各自微笑转身走入人群。
这段坑死人的对话大约来自于英语课本。有个笑话说,有个中国人到美国旅行,不小心掉进井里,一个美国人来了想帮助他,问道“Hi,how are you?”这位中国人很激动,回答“Im fine,thank you.”结果,这位中国人死了。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翻看我们的汉语课本,有一些会话素材日常生活几乎不用,居然需要老师大讲特讲。有人调侃说,中国文化就是吃文化:谋生叫“糊口”;工作叫“饭碗”;受雇叫“混饭”;靠积蓄过日子叫“吃老本”;混得好的叫“吃得开”;占女人便宜叫“吃豆腐”;女人漂亮叫“秀色可餐”;受人欢迎叫“吃香”;受照顾叫“吃小灶”;不顾他人叫“吃独食”;没人理会叫“吃闭门羹”;有苦难言叫“吃哑巴亏”……
依我看,学习汉语的第一句话应该是“吃饭了吗?”
那些匪夷所思的问题
《楚天都市报》曾邀请五名外籍友人就高考英语试题进行“考试”。其中三名是外国留学生,两名是英语外教。这五人中,三人以英语为母语,另二人来自南非和俄罗斯,以英语为自己的第一外语。测试结束,得分最高91分,最低71分,平均79分(按总分100分计算)。
网上有个段子说:等咱中国强大了,全叫老外考中文四六级!还有人设计了这么一段中文对话做听力材料:
男:你的牙很好看。
女:假的。
男:真的假的?
女:真的。
请问:她的牙是真的还是假的?
生活中类似的对话还有:我差点摔倒vs我差点没摔倒。有没有摔倒?
在一个汉语教师口中,这样的用语是要封杀的,不然会给老外一种不负责任的感觉。
中国人为什么买“东西”,不买“南北”?中国人对这些问题习焉不察,但是老外会问。这个问题有两个解答:
一是语源出自盛唐时代的首都长安城。长安皇城位于北部,其余区域遍布着坊、市。坊与市呈长方形,四周围以高墙,区划整齐,分东西二市,是规模庞大的东西方商品集散地。东西二市之外是里坊居民区。唐人购物必须上东市或者西市去,故曰“买东西”;
二是南宋理学大家朱熹未出仕前,在巷子里遇到博学多才的好友盛。盛手中拿了一个竹篮,朱熹问他:“你去那里?”盛说:“我要去买点东西。”朱熹很好奇,随即问道:“你说买东西,为什么不说买南北呢?”盛反问朱熹:“你知什么是五行吗?”朱熹答:“当然知道,不就是金、木、水、火、土吗?”盛说:“东方属木,西方属金,南方属火,北方属水,中间属土。我的篮子是竹做的,盛火会烧掉,装水会漏光,只能装木和金,更不会盛土,所以叫买东西,不说买南北呀。”
学汉语到底难不难?我经常会被老外问这样的问题。我负责任地说,学汉语不难。我的韩国学生朴灿柱去年9月入学,汉语几乎是零基础。经过一个学期的学习,他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汉语水平三级考试(HSK),满分300分,他得了270分。600个汉语单词听、说、读、写无压力,是中国大学中文系入学的最低语言标准,但比同样的标准要求中国人学英语达到这个水平,不甚容易。
从语音上来说,汉语更算不得复杂的语言。汉语有声母22个(包括零声母)、韵母24个、声调4个,而泰语有辅音44个、元音32个、5个音调。
汉语哪儿难了?汉字!我在课堂上做了一个调查,了解学生对汉字形体的认识。我在黑板上写了两组字,第一组是“玖”和“集”,第二组是“红”和“江”。我问学生,这两组汉字中哪两个比较简单。答案是“玖”和“江”。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学生对汉字繁简的区分标准非常简单,那就是笔画的多少和线条的曲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汉字的繁简并不能增减汉字的学习难度。
学生都觉得“一”比“壹”简单很多,他们畏惧的是汉字的形态而不是某一个汉字。好在我们的祖先不是毫无根据地创造汉字的,比如和“贝”有关系的字词基本都和钱有关系。和“木”有关系的字词基本和树都有关系。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他们会对这种强大的组词能力感到吃惊。
我的中国梦
有一天,辜鸿铭坐在电车上看伦敦的《泰晤时报》,几个同车的英国人觉得好玩,侮辱辜鸿铭。起初,辜鸿铭不理他们,后干脆把报纸调头来看。那几个英国人更来劲,说:“看,那个中国小子连字都不认得,还看什么报纸?”这下把辜鸿铭给惹火啦,他用纯正娴熟的英语把整段文章念出来,然后说:“你们英文才26个字母,太简单。我要是不倒着看,那就一点意思都没有!”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如果不是走出国门从事对外汉语教学,我不会发现我的梦和“中国梦”如此紧密相连。汉语作为“爱国主义”的符号,融入了近代中国人百年的情感之中。一个国家只有强大,她的语言才会受到尊敬。
2012年,我在泰国教中文。春节期间,学校让我做一块宣传春节的展板,中文教学组主任却提出了一个匪夷所思的条件:不得在展板上出现“龙”字,也不得在展板上出现龙的形象。她是基督教徒,她认为在《圣经》里面,dragon是邪恶的象征。
我反复向她解释,西方文化里面的龙和中国文化的龙完全就是两个事物。西方的龙喷火,中国的龙喷水;西方的龙有九个头,中国的龙只有一个头;西方的龙有翅膀,中国的龙没有翅膀,是中国人传说中的守护神等等。所以把中国的龙翻译成dragon是不对的,就好像你们把我们的壁虎翻译成了蜥蜴。应该直接翻译成“long”或者类似于这样的发音才对。
她接受了我的解释,最终我们得以在学校的报刊亭里张贴一副龙的图像,直观地把一些春节元素展示给泰国学生。
因为交流,我们学校的主任知道中国的“龙”并不邪恶;因为莫言获奖,汉语作品被更多的人阅读;因为中国有了载人航天飞船,英语当中出现了一个新的单词———Taikonaut……随着中国的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分布到世界各地,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学习汉语、了解中国。语言往往承载着文化,只有更多的汉语词语通过直接准确的方式呈现给世界,才能减少误会和纠葛。
看到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学习汉语了解中国,我深感自豪。我愿意为实现中国梦付出双倍的努力,因为这个梦同样属于我。(责编 张圣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