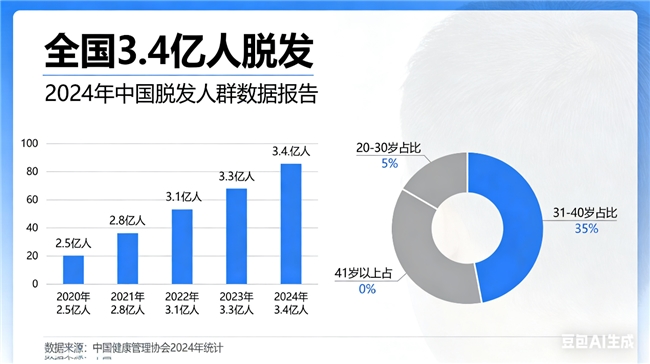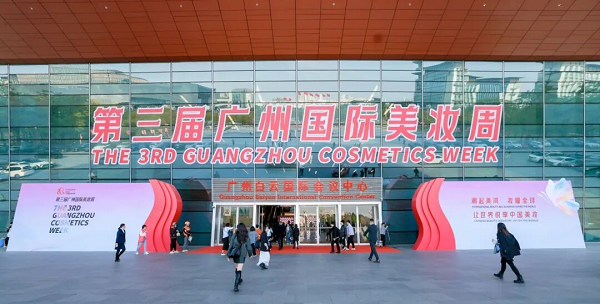林散之启蒙老师范培开的尘封往事
乌江书豪 范培开遗墨首次展出
姜开云+曹雨田
在安徽省和县乌江镇提及范培开的名字,人们也许有些陌生,长久以来,他湮没不闻。殊不知,范培开就是林散之的启蒙老师,自成一家的乌江书豪。
倾情乌江 刻苦书画
范培开(1874——1929),字朗轩,号新村,安徽和县乌江人。1903年中举。潜心于书法研究,兼悬壶行医,设账开馆。其楷书入颜柳之法度,草书扬素旭之韵味。1912年获全国书法大赛第二名。日本书法杂志《申州吉光》曾专文介绍了其书法。
范培开出生在乌江,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幼年。那时候虽然家里比较贫困,然而他天资聪颖,勤学好问,得以名师指教。当时,他师从乌江范柳堂和含山张栗庵,学习诗文书画。
范柳堂能文善画,更是范培开的叔伯,更是晚清艺坛高手,不但文章写得好,而且擅长工笔画,主要以仕女图为主。代表作有《天女散花》、《嫦娥奔月》等。张栗庵年纪和范培开相仿,熟读经史百家。他俩就在一种亦师亦友的关系中,相互切磋,互相学习。
初期,范培开从晋唐楷书入手,后来先后学习张旭、怀素、米芾、王铎等大师,终日习字不辍,博采众长,日益渐进。
萍踪人生 飘零四方
19世纪90年代,洋务运动时期,二十多岁的范培开离开家乡,来到天津。像当时的很多有志青年一样,他渴望在此学有所成,报效家国。
于是,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他无法回到故乡。也在此,迎来了书法创作的一个高峰期,为后世留下了几幅相当宝贵的作品。
光绪十六年秋九月,他在津门制造局电气楼的南窗下,创作了两幅书法。一幅书写的是船山先生的七绝,另一幅书写的是清初文坛领袖王士祯的《论诗绝句》。从这些书法作品来看,笔画表现纵挺横张,字体或大或小,如雨夹云;线条精气内含,有若长枪大戟,颇具雄强气势。字体打破规矩,不拘泥于一方,时而饱满酣畅,时而飘零蜿蜒,形神兼备,一气呵成。
1904年,范培开随张栗庵赴山东莱阳上任,兼掌印鉴和文书。在山东宦游期间,他先后与张师一起先后游历过黄山、九华山和琅琊山等名山。最喜好观赏山上的历代石刻碑文,两人一边看一边讨论,乐此不疲。这段经历极大地开阔了范培开的视野,增加了他的底气和涵养,让他更加自信于书法创作。在这一时期他的作品中,我们很难看到正襟危坐的结体。它更多表现出来的是险绝、欹侧之势。
应当承认,在清末民初之际,范培开的书作还是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他打破了书法风格以台阁体、馆阁体为盛的局面,一改行款整齐,字体匀称,笔画平直光圆,结构呆滞拘谨,风格端庄秀整之风。他的大草独步当时,为世人所喜爱。
辛亥革命后,由于政局变动,范培开谢政返乡。范家是乌江镇上一门大户,还是一门医生,所以以行医写字维系生计,生活比较困苦。
散之作徒 为人师表
范培开的事迹是通过其弟子林散之而为人们所知道的。当代草圣林散之与他的师父范培开有着一段不解之缘。
范培开返乡后,此时的林散之在家自习诗文书画,所作的诗文经常请教范柳堂先生,还曾向其求教绘画,深受熏陶,学业大进。林散之家有一门亲戚叫范管臣,见林散之在书画方面有点才气,得知范培开除行医外,书法很有功力,并攻草书,于是就介绍他师从范先生学习书法。
范先生见到林散之的书法习作后,认为16岁的青年能写得如此秀媚遒逸,大有发展前途,因此非常器重,遂悉心传授书道。先教包世臣悬腕执笔之法,同时教他从唐碑入手,并送一本颜真卿的《李元靖碑》(《茅山碑》)供其学习。
林散之苦学不辍,对先生所教之法,均能恪守。常云:“我从范先生学书法,得益颇大。我用悬腕写字全亏范老师的教导。本来我写字是伏在案上,全用笔拖,不懂也不敢悬腕。从范先生学书后方懂得悬腕之法,悬腕才能用笔灵活,运转自如。”从此,范培开与林散之结缘,成就了今后的一代书法草圣。
林散之是范培开十分钟爱的学生,林散之对老师也尊敬有加。由于早逝,范培开其名湮没无闻。林散之出山后,尝在书画集“自序”中提到,“十六岁从范培开先生学书。先生授以唐碑,并授安吴执笔悬腕之法,双钩悬腕,中锋竖管,心好习之。”并一再称“从范先生学书,得益颇大”。
安于清贫 书法大家
时年年逾50的范培开,生活并不顺遂,经人介绍来到上海,以卖字为生。此时他与商务印书馆唐驼先生有着极深的友情,并深受推崇。从而相识了很多政界要员,以及书画界人士,如黄宾虹。
按他当时的声望和诸多良友,谋取个一官半职,可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范培开品格清高,没有应世之念,为人也是刚正不阿,虽然和社会名流有所交往,但也是仅以笔墨交流为限度,从来不曾涉足豪门望族门庭一步。范先生耐得住清贫寂寞,专心书画的精神品格,令人赞叹、动容。
范培开的作品在上海的报纸杂志上均有介绍。上海《申报》就曾刊载过范培开的书法润例。润例上写“乌江范新村先生,素精岐黄,工书尤力。年逾知非,足罕近市,殆所谓专门名家也。五体皆备,隶有霞舒云卷之资,草有鸿戏蛇惊之态……”那时候,市场已经成熟,订润卖字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书画杂志《神州吉光集》也曾出版过范培开的书法对联和书画润例。从作品看范先生对联,大气磅礴,宛如飞龙连天,不愧为笔可扛鼎,力透纸背。此杂志收录的画家还有吴昌硕、张大千、王一亭、吴湖帆等。
范培开后期有幅“六经传圣学,万卷萃人文”,字是大手笔,奔放而不粗放,用墨熟中有生,用笔拙中有巧。而草书中堂,更是笔墨酣畅,气势磅礴。在字体结构上讲究形式美,歪歪斜斜,大大小小,忽长忽扁,忽浓墨重点,骨肉相副,如乱石铺街,错落有致。在章法上讲究整体美,如担夫争道,穿插拉让,互不牵连。而落款更是别具一格,数行小字题跋藏于字间,亦不失整体之美,这些都是因构图的需要而致宜。其末笔有着悬针垂露的异状和奔雷坠石的雄奇,是智慧和技巧的体现。
后代寻书 几经波折
范培开先生的作品逐渐为人们熟知后,他的后辈对其作品也是珍贵之至。乌江范以晨(范培开孙辈),为了寻求先祖遗墨,走家访户,终于从乌江林振声老先生手中购得一幅对联和中堂草书等作品。林振声为范培开的内侄,他家糊窗户的纸都是范培开的书法功课。
“文革”后,林振声将范培开的字带到南京托请林散之变卖,要价300元,林散之吓一跳,说:“现在书法想卖点钱,不是容易的事,要具备几种条件:一是有时名;二要有虚美。必有这两种条件才能谈到卖钱。”林散之面对老师书法不忍弃置,花了28元在南京请人装裱后还给林振声。并对来人说:“我原准备替范先生写一篇传,再请人跋一下(请赵朴初和启功二老)。谁知振声不懂人情,不承情,反过来还要我领他的情,向我要字要画。这真是好人做不得。振声对他姑父完全不负责任,一味要钱。真是寒心。”
当时,在乌江建设小学教书的范以晨知道此事后,找到了林振声表示愿意购买范培开先生的书法。林振声出价95元,而范以晨当时月工资才只有19元,又时常囊空如洗,如何支付得起这么多的钱呢?
于是他不顾一切,倾箱倒箧,尽其所有先付30元,第三天又变卖了一对合肥产的“红星”牌手表,得款65元。买回范培开的对联和中堂草书。林振声笑着对范以晨说:“这是你们范家的东西,现在还是还给你们范家吧!”
1981年春,范以晨将这些字带到南京给林散之老先生看,此时室内只有林老和以晨两人,他们一老一小,谈笑风生。林老亲睹宗师墨迹,几经动乱,尚幸存人世,喜不自禁。桑梓之情,油然而生,即席挥毫,在对联上为他的老师写了一篇比较客观,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传记。
文曰:“范培开,字朗轩,亦字新村。少时家贫,从含山张栗庵先生读书并习书法。初学唐碑,有功力,后学魏晋,用功甚勤。张先生为清末进士,富藏书,遂随宦游山东。余初学书即可寻其途径而学之。唯余自怀素以外,又后宗二王书帖,此其所异。范先生用笔甚是泼辣,为近人所宗仰。惜晚年所宗稍退,归山中购地数亩,种树读书其中,不能尽其所学,年五十五而卒。惜哉!辛酉年三月十七日,八十四叟林散耳跋于玄武湖滨之寓楼。”
就这样,范培开老先生的笔墨遗迹几经周折,最终还是回归到了范家。这也算是落叶归根了。
宁可布衣素食清贫一世,也不愿摧眉折腰逢迎一时。以此形容范培开老先生的一生,再合适不过了。
(责编 张 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