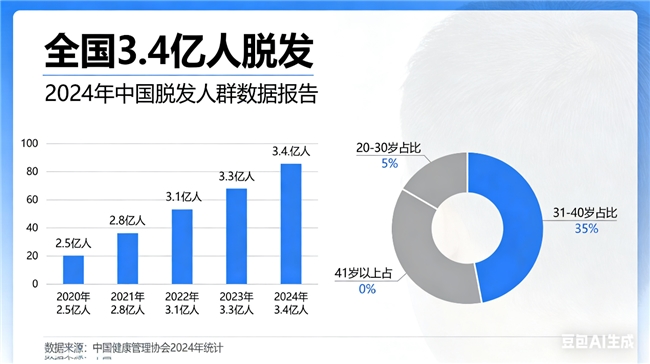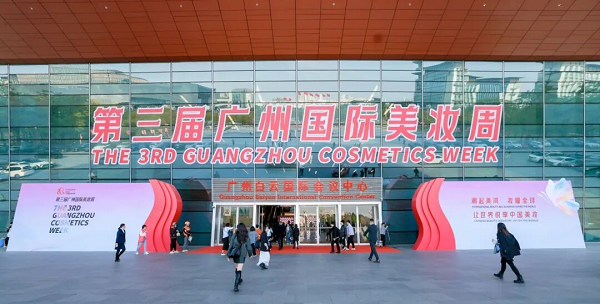古巴:被时光遗忘的“加勒比明珠”
陈婷
社会主义国家、卡斯特罗、切·格瓦拉、导弹危机、海明威、雪茄、朗姆酒、萨尔萨舞,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一道道标签张贴在这片加勒比海群岛上,散发出一种神秘气息。老哈瓦纳街道两旁的西班牙阳台、特立尼达的碎石小径、西恩富戈斯的法式街道,交融在一起,给旅人一种特别的诱惑。
古巴的货币
古巴货币单位是比索Peso,分为红币CUC(Peso Cubano Convertible)和土币CUP(Moneda nacional)两种,红币是可兑换的外币(相当于我们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外汇券),和欧元的兑换比例基本是1∶1,外国人在古巴只能使用红币,酒店和机场、银行都可以兑换,机场稍微贵一些。土币是当地人使用的货币,也可以和红币兑换,比例是25∶1。古巴的消费水平内外差别很大,如果本地人花十个土币打车,那么外国人就是十个红币,相差二十多倍。对于外国游客来讲,旅行消费还是蛮高的。
Wifi网络
古巴政府仍禁止个人安装家庭网络,街边热点成了人们上网的主要途径。2015年3月,哈瓦那才出现首个提供无线网络的公共场所,Wifi密码是革命口号“在这里,没有人投降”。国有电信公司Etecsa在古巴建了35个Wifi热点,在此之前,互联网属于特权人群,比如官员、工程师、医生、大学教授,还有外国游客等。但是付费Wifi十分昂贵,每小时上网费用两美元,如果从“黄牛”手中购买上网卡,每小时是三美元,所以每次上网后一定要记得断网下线。
交通出行
当地人的公共出行主要依靠两种交通工具,一种是公共巴士,但几乎没有站台和站牌,需要依靠记忆在固定的地点等车,这样的交通对当地人不是难事,对于游客来说基本无法采用。第二种便是按照固定线路行驶的分享出租车,在线路上招手即停,时常会非常拥挤,但费用也相对便宜。街边经常会见到要求搭车的当地人,古巴政府规定,只要是公家车,路遇要求搭车的人不可以拒绝,而且免费。
哈瓦那 迷失之城
哈瓦那,我的镜头从古迹建筑转向生活在里面的人们,一幅幅浓厚生活气息的画面跃然而出:杂货店前的长队,坑洼不平路面上穿梭的三轮车与老爷车,街道上玩耍的孩子们,工艺品店里的切·格瓦拉肖像,巴洛克古典建筑的阳台上晾着的各色被单……
哈瓦那分为两个部分,西班牙殖民时期修建留存下来的老城(当地人称“老哈”)和美国管控时代修建的新城。然而无论是老城还是新城,1959年古巴革命以后基本都没有新建建筑。这些老建筑物的破损状况非常严重,昔日那些美丽的浮雕装饰的墙壁古典韵味十足,然而岁月太无情了,不少建筑物上长满了野草,甚至从顶楼生出大树,昭示着这里已经走远的历史。
游走在老哈的窄小街巷里,街角飘出的欢快音乐将我带进了昔日美国大文豪海明威经常光顾的地方——“五分钱小酒馆”。不过几平米的小酒馆儿挤满了游客,点上一杯古巴鸡尾酒“莫希托”(Mojito),海明威的最爱。导游小声说,这家的Mojito其实味道很差,就是名气响,我心领神会。不过小乐队还是不错的,热情的笑容,很有感染力。
老城的色彩是丰富的,也是陈旧的,炫目而憔悴。每当看着那些上百年历史的老房子,便心生惋惜,如果搁在别处,好好维护,一定非常美丽。哈瓦那,或许是世界上少有的没有肯德基、麦当劳等国际连锁快餐厅的国家首都,也见不到铺天盖地的巨幅广告,墙上的领袖像和革命壁画无声地拉开了古巴和其他美洲国家的距离。
“这些都是在旧报纸上画的油画。”街边的小贩向我兜售着粗糙的工艺品,报纸上画着色彩艳丽的老爷车和窈窕女郎,革命古巴的另一面。除了老爷车,最常见的贩卖元素还有切·格瓦拉。如果说其他国家使用这位偶像级的革命家形象还有些矫情的话,古巴,最理直气壮,然而格瓦拉在自己的祖国阿根廷无人问津。
现在的古巴人口中,白人占73%,主要是西班牙人后裔;黑人占13%,是18世纪初至19世纪末被贩卖到古巴的60万非洲奴隶的后代;此外印欧、黑白混血和其他人种占14%。人种的多元化必然导致文化的丰富和多元。
城虽破,但生活在里面的古巴人的日子却过得有滋有味。孩子们在街道上玩耍着,享受着物质贫乏的快乐童年;大人们三五成群在路边闲聊,街边经常可以看到围着桌子打牌的人,这种牌很像中国的麻将,只是游戏规则要简单许多。我诧异于他们的这份淡定和怡然自得,甘心于物质生活的贫乏,愉快的面貌和破烂的城市形成鲜明的对比。
这种反差一方面我归结于海岛人的性格,有音乐和阳光,加上基本的生活保障,日子还是可以过下去的;另一方面,便要归功于老卡的领导了,古巴有一种顽强的精神,经受住了时间的挑战,不是十年八年,而是半个多世纪,政权依旧稳定,虽然改革迫在眉睫。
特立尼达 一日百年梦
特立尼达是古巴的一面镜子,你可以看到過去、现在和未来。
特立尼达(Trinidad),古巴第三古老的城镇,这是仅次于哈瓦那的最吸引摄影师的人文古城了。
四通八达的鹅卵石街道凹凸不平、坑坑洼洼,自19世纪延用至今,完全没有修缮过,早都被岁月磨得光滑,在黄昏的暖光下映射着迷人的光泽。这样的街道搁在别处,早就围挡起来,禁止行人踩踏了。然而,这里,汽车、马车、三轮车照驶不误,完全不在意脚下珍贵的历史古迹。其实走在上面并不舒服,还有些硌脚,但立刻把人拉回百年前,那种感觉还是很特别的。
受益于蔗糖贸易的繁荣,这里曾经繁华一时。19世纪特立尼达涌现了一批带有殖民风格的巴洛克式或新古典主义的大型建筑,建于17、18世纪的老旧房屋也被重新改造,这里变成了古巴人均石瓦房最多的城市。1868年,古巴独立战争开始,持续三十年的战乱摧毁了大部分的蔗糖种植园和制糖作坊,城市走向衰落。钟摆也停在了这个时期,此后的特立尼达再无更多发展,于是完好地保留了从16世纪到19世纪的殖民地建筑风貌,21世纪的高科技似乎被一种力量隔绝在外,一切都没有改变。
游走在小城各个角落,我试图捡起百年间碎片式的记忆。站在大广场(Plaza Mayor)前,立刻有种回到鼎盛时期的西班牙殖民王国的感慨。圣蒂斯玛·特里尼达教堂(Santísma Trinidad church)和Palacio Brunet宫是这个城市最重要的建筑了,尤其是后者,现在改成了博物馆,不知谁起的名字——Museo Romántico(浪漫博物馆),其中之陈列却并非什么浪漫爱情之类的物件,而是特立尼达自建立以来所走过的历史轨迹。博物馆的钟楼是特立尼达的最高建筑,耀眼的黄色很醒目。我爬到顶上,俯瞰小镇全景。远处起伏的山,近处优雅的建筑,红瓦白墙,尽收眼底。
漫步在夕阳余光下的小巷,穿梭在浓浓殖民风的建筑之间,身边来来往往那些刻画着沧桑的面庞,这座昔日的蔗糖重镇,如今的旅游大热门地,也是一个充满色彩、冲突和变化的地方。
海明威故居行
古巴,参观海明威故居,走进大文豪昔日的生活,我不知道还有哪个大作家可以像海明威一样,过得如此活色生香,丰富多彩。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我走进哈瓦那郊外San Francisco de Paula的瞭望山庄(Finca Vigía),大文豪海明威的故居。海明威在古巴生活了二十二年,刚来的时候,他一直住在酒店,直到同第三任妻子玛瑟结婚,玛瑟不愿意住酒店,在报纸上发现了一则出租庄园的广告,于是她说服了丈夫,1939年以每月100比索(与美元等值)的价钱租下了瞭望庄园,一年以后又用1.85万比索买下了庄园的产权。
海明威去世后,古巴政府说服他的遗孀“捐献”出故居,之后被妥善保护起来,1962年成为博物馆。印象最深的有两处,一个是書多,七千多册书分散在各个书柜中,书房一隅有架老式的“罗亚尔”牌打字机,海明威便是用它完成了《老人与海》等脍炙人口的作品。据说他喜欢站着写作,通常脚穿一双特大号运动鞋,踩在一张羚羊皮上,对着打字机和齐胸高的读书板就开始工作了。
另一处则有些不太符合他的文人身份,墙上一个巨大的羚羊头吓了我一跳,仔细一看,屋内还挂着不少战利品:野牛头、豹子头、老虎头等,都是他数次去非洲打猎的“战果”。谁说文学家一定是个文弱书生?海明威就“文武双全”,他喜欢冒险,钓鱼、斗牛、打猎样样在行,两次参加世界大战,还有西班牙内战,获勋章无数;战场上受伤,开过12次刀,取出237块碎弹片;到英国乘轰炸机升空助战,到中国深入陪都重庆采访助战,在古巴驾船追逐纳粹潜艇助战;口诛笔伐德国纳粹、西班牙的“第五纵队”;曾钓过7米多长的大鱼;去非洲打猎时飞机失事,成为生前能读到自己讣告的极少数作家之一;有过四任妻子和众多年轻貌美的情人,他笔下塑造了一系列打不垮的硬汉英雄,最终却用心爱的双管猎枪自杀。他用自己的一生及作品诠释“硬汉”的含义。
海明威在古巴的生活多姿多彩,庄园里,他饲养斗鸡、猎犬和猫,苦练拳击,与附近的孩子们组织了一支棒球队;他大抽雪茄,痛饮朗姆酒;他经常身着瓜亚维拉衫(一种加勒比地区流行的绣花衬衣)、脚踏软鞋驱车前往“小佛罗里达餐馆”、“街中小酒馆”,或前往柯希玛尔乘上自己的“皮拉尔”号游艇出海钓鱼。当然,最重要的是完成了《丧钟为谁而鸣》和《老人与海》,迎来普利策奖和诺贝尔奖,他甚至把诺贝尔奖章赠给了古巴城市圣地亚哥,放在当地的圣徒贞女的神龛里。他一方面尽情享受生活,另一方面对这个世界的不公与不义也从不曾置身事外。但他从不愤愤然,从不吐槽抱怨,始终保持着一个记者的冷静,以及一点儿那个时代才有的自嘲与冷幽默。
“人生来就不是为了被打败的。人能够被毁灭,但是不能够被打败。”站在这个上世纪传奇人物的故居里面,这一点尤其让人印象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