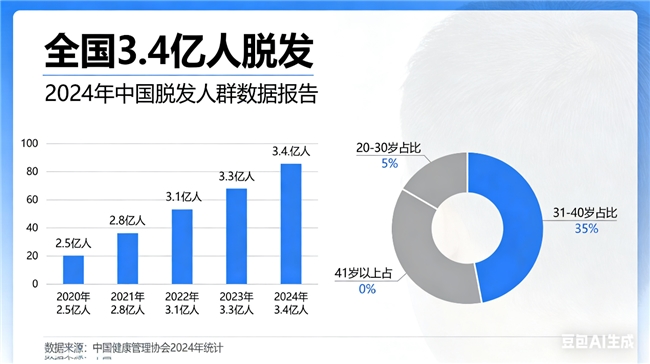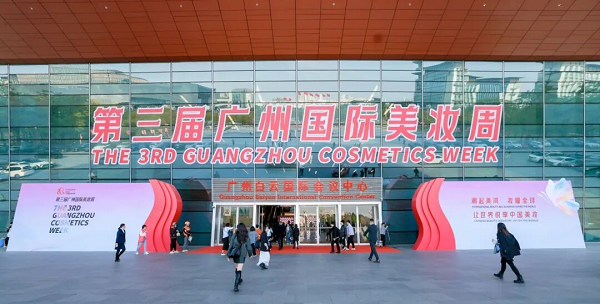谁是多余的
蒲末释
我一直挺恨你的,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个陪衬品。我们中有一个是多余的,对吧?
猜猜我是谁
来,我们玩个游戏,叫做:猜猜我是谁。秋年总是笑着拉着秋成站在人前,他俩对视一眼,狡黠一笑,站定了,就不说话。
秋成和秋年是一对双胞胎,秋年是哥哥。两人从小衣服鞋子都是同套的,外人总是分不清谁是谁。有时晚上睡觉,秋成翻一个身,两张脸相对着,他都分不清到底睡着的那个人是自己还是醒着的人是自己。他问过秋年是否也有同样的感觉,问的时候小心翼翼的,在他心里这只能是属于他俩的秘密。但秋成说他没有,还学着大人的口气让他不要想这些乱七八糟的问题。
从那个时候起,他就开始讨厌秋年,讨厌他那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每次父亲从工地回来,他俩就站在父亲面前,一个拉左手,一个拉右手,顺着步子绕几圈,然后让父亲猜,最初他总是笑呵呵的,可后来次数多了,父亲就会显得不耐烦。有一天他回来得比较晚,他们又拉着他玩这个游戏时,秋成被父亲扇了一巴掌,“秋年你就不能懂事点!”
“是他,他才是秋年!”秋成哭喊着嗓子,一眼的委屈泪哗啦啦直流。父亲瞪了他一眼,咬着唇腮,扬手又要给他一耳刮子,被母亲及时拦住了。秋年却躲在父亲身后,呲牙咧嘴地朝他笑。
后来一起上学的路上,秋成开始故意走得很慢。他不想和秋年出现在同一场合,却又不得不与他在同一场合出现。他俩在同一个班级,每次同学拿双胞胎说笑的时候,捉弄的都是他。他们会故意喊秋成的名字,他不答应他们就一直喊,他答应了,他们就说:原来你不是秋年啊。
这种无聊把戏,秋年却从不中招,有时候他还会故意跟那些人一起捉弄秋成,连秋成说话的尾音他都能学到,秋成只能百口莫辩,等他们失了兴致,自然就不拿他当猴耍了,他只能这样想着。
秋成不知道为什么在玩这种游戏时总是会输给秋年,那晚出生的几分钟似乎是一种冥冥注定,他只是秋年的一个复制品。在外人看来,这个复制品近乎完美,可只有他自己知道不是,从小到大,秋年都比他招人待见,成绩比他好,跟长辈说话也大大方方的,秋成最多只能是算一个陪衬,一个完美的陪衬。
我要留级
这种日子一直持续到五年级,秋成从同学的课余闲谈中听到的一个消息:如果这次期末考,考了倒数第一,就有可能会被留级。“跟下一届一起读,多丢人啊!”他们吵嚷着,然后就散了。人们对这种听闻来的“坏事”,从来不会往自己身上揽。
秋成却听了进去。他决定留级,为了摆脱秋年。那次期末考,秋成把自己会做的题都填了错的答案,结果真的考了班级倒数第一。他没把成绩告诉父亲,也央求着秋年别说。
“你是故意的吧,你的卷子我都看了。”秋年直勾勾地望着秋成,显露着他一贯的高傲。“你,你有跟其他人说吗?”秋成没敢看秋年的眼睛。“没有,怎么说,你也是我兄弟。”秋年带着一丝戏谑笑着说。“嗯,谢谢。”秋成第一次觉得秋年没那么令人厌恶。
那天晚上,秋年睡觉的时候问秋成:“你故意考得不好,是想要留级吧。”秋成听得心里一惊,原来自己在他眼里什么都瞒不过。“不是,我只是觉得好玩儿。”秋成语气强硬地说着,新找的这个理由让他松了一口气,可他又明白这个理由连自己都说服不了,转了一个身,侧躺着,假装睡了过去。
“其实,我也不是很想跟你待一个班级,倒不是针对你,我自己也能自由些。”秋成听着秋年说着,听到自由这个词时,他有些想笑,这个在课本上看起来简单而被歌颂的词,令人费解而又莫名神往。“秋成,你有想过,我们两个,有一个其实是多余的吗? ”那似乎是秋年的一句梦呓,秋成转过身,秋年已经打起了呼噜。
父亲得知秋成的成绩时,气得脸上的青筋暴起,抡起手边的扫帚就打。捱了一顿打,可秋成心里舒坦,在父亲拿到成绩单前,班主任已经宣布了要他留级。
秋成挨打的时候,秋年躲房间里去了,等秋成回房间,他偷偷塞了两包跳跳糖给弟弟。秋成接过去没说话,拆开一袋,吃了两颗后,塞了秋年一颗,两人看着对方笑了起来,又不敢笑大声,怕门外的父亲听到了,又是一顿打。
秋年说:“下次他打你,你就拉上我,我替你挨打,反正他分不清我们谁是谁。”
那场意外
七月中旬,荷花满池塘开了,秋年带着秋成去钓龙虾。他们钓完龙虾,就去河边洗澡,秋成却站在岸上。每年夏天他都会听母亲讲不能去河边玩水,要是被父亲知道了,保准打断一条腿。
他们招呼着秋成下岸,秋成直摇头,他们说他胆小鬼,他也不反驳。只看到秋年跟几个年龄稍大的赤溜着身子,往前蹭着,激起一大片水花。“秋年!”秋成喊了一声,他又不知道说些什么。“没事!”秋年回头笑笑,继续往前潜着。
灼烈的太阳晒得人头皮疼,河中央溅起的水花泛着刺眼的光,不知是谁在秋成身后推了他一把,他只觉得重心不稳跌进了河里,只是在河岸边,瞬间裤脚全湿了。“秋成下水咯,秋成下水咯!”有人叫喊着,岸边几个人拉着他继续往前走。有一只手在他的腰间猛烈一推,他整个人的身体往前倾去,脚下突然变得空荡荡的,身体猛地往下坠,鼻孔被一股柔软而充实的东西堵住。水从嘴里涌了进去,朦胧中他踩到了一块石头,感觉鼻子浮上了水面,却呼不到一丝空气,又沉了下去。
“秋成!”他似乎听到秋年喊着。“秋成,你等我!”秋年似乎带着哭腔。秋成觉得浑身失去了力气,水依旧大口地涌进他的嘴里,充积着他的胃。恍惚中,他感到一只手,用力托着他的脖子,那股力量支撑着他,缓缓地往上,到最后稍稍松弛了一下。
秋成得救了,但秋年死了。岸上的人说,秋年一个劲地托着秋成往岸边冲,自己力竭沉入水底。后来慌乱中顾着秋成,就忘了还有一个秋年。
“他有喊我名字吗?”秋成在后来问众人。“没有。”他在水里游那么快,说不了话的。“可是,我明明听到了,我听到了的。”秋成呆呆站在那儿,自言自语。
那一年,双胞胎十二岁。之后秋年的所有东西,用的穿的,都被母亲偷偷烧了。从那天起,母亲再没跟他说过一句话,父亲一日日地喝酒,喝掉了工地的工作。
秋成的十四岁生日,母亲买了一些菜,吃饭的时候,她一直叫秋成多吃一点,说着说着她就嚎啕大哭起来。父亲抽着烟回了房间,他听见拳头擂墙壁的声音,一声又一声。
下午,秋成一人出了门,他闷着头一直走,再抬起头来已经是秋年的墓前了。这条路,他走了太多次了。秋成蹲下身,用手去抚拭那墓碑,上面有他的名字“秋年”。
他想起他们都说过的那句话:我们中,有个人是多余的,不该存在的。